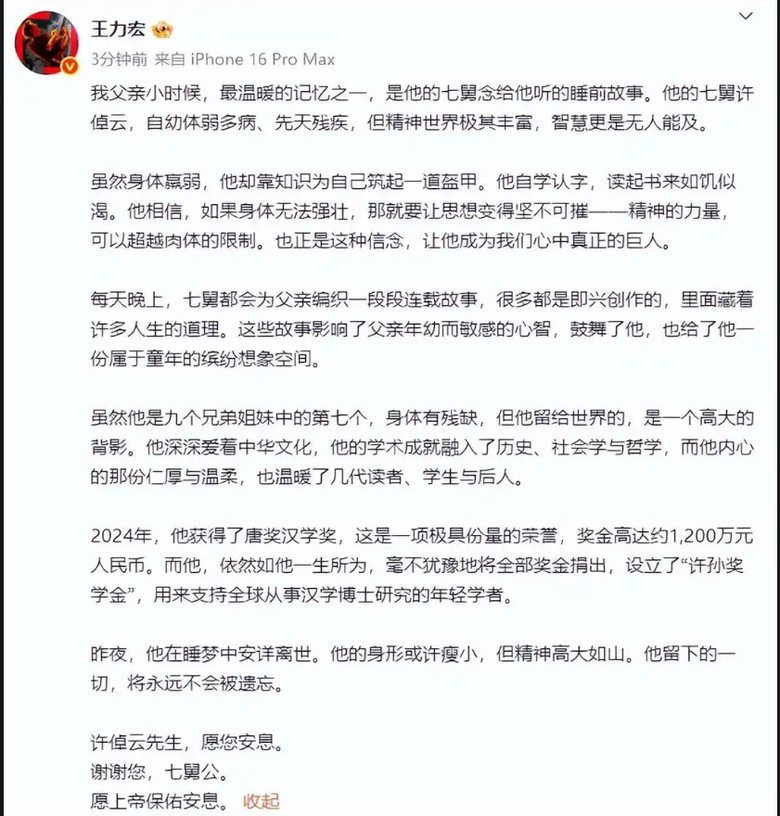歷史學者許倬雲過世了,享壽九十六歲。
他一生的確留下了豐富的學術著作,對中國古代社會、制度與文化的研究頗具啟發性,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研究中國史的學生。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,他都是一位學術界的重量級人物,這點我必須尊重與肯定。
但作為一位在台灣讀書、留學德國、在電機資訊領域耕耘數十年的人,我更關心的問題是:
他究竟是如何憑藉台灣這個身分,在中美對抗與冷戰體系中,走出自己的學術道路?
又是如何在這個過程中,一方面否定台灣的存在價值,一方面卻始終未曾真正回到他口中的「祖國」?
許倬雲在晚年常說,他「希望死在中國」,那裡是他的文化根,是他心靈的歸宿。
然而他真正居住超過六十年的地方,是美國。他的學術資源、學術自由、生活條件,都是美國提供的。他享受著美國的民主制度與學術獨立,卻常公開歌頌中國的文化厚度、講台灣是沒有文化的社會,甚至對中共政權的批評也十分保留。
他沒有回中國,也沒有死在中國。他留在美國,死在美國。
這不是什麼私事,而是一個象徵:他從未真正願意承擔他所嚮往的「中國」帶來的現實代價。
許倬雲從中國逃到台灣,再從台灣出國,赴美深造。這樣的歷程,在1949年後的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當中並不少見。他們靠著台灣當時的制度、資源與國民身分,取得出國留學與學術網絡的門票。
但他後來的發展,幾乎與台灣切割。他在國際上代表的是「中國歷史學者」,卻不是「來自台灣的知識分子」。他關心的也從來不是台灣的現代化歷程、民主轉型或本土文化,而是如何讓「中國文化」在世界文明中不被邊緣化。
他是一個「文化中國」的說書人,而不是一個「民主台灣」的見證人。
他享受著美國的民主制度與學術獨立,卻常公開歌頌中國的文化厚度,甚至不吝於批評台灣是「文化沙漠」,說「台灣只有三代人,有什麼文化可言?」——彷彿台灣人的語言、信仰、文學、歷史記憶都不算數。他對中共政權的壓迫與謊言輕描淡寫,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卻嗤之以鼻,曾說過「民主不是什麼好東西」,讓人不禁懷疑他所嚮往的「中國」,究竟是一種文化記憶,還是一種封建幻象
而當他們回過頭,看到一位在美國一輩子生活的學者,不斷對媒體說台灣沒文化、沒根,卻從不敢真正面對中國的現實時,他們心裡的疑問我聽過很多次:
「老師,這樣的人,為什麼被一堆人視為國寶?」
許倬雲的去世,象徵的是一種「文化中國想像」的結束。那是一種以中華歷史為榮、以文化厚度為價值判斷標準的世界觀。這樣的世界觀,曾讓他們在國際上獲得地位,也曾讓台灣在冷戰體系中被當成「中國的代理人」而獲利。
但今天的我們,已不再依靠那樣的身分。我們靠的是自由社會的制度、透明的競爭、與開放的創新環境。我們的文化,是從生活中長出來的,不需要「夏商周」背書。
許先生走了。對於他一生的學問,我給予尊敬。
但對於他對台灣的冷漠與偏見,我也不會噤聲。
因為我們是新一代的知識分子。
我們相信,真正的文化不是靠血統延續,而是靠選擇與實踐累積而來的。
我們選擇台灣,選擇民主,選擇一條沒有祖國庇蔭的自主之路。
那就是我們與他最大的不同。
他說台灣沒有文化,但我們在科技、藝術、民主制度中,看見了文化正在發生。
他死於美國,懷念中國;我們活在台灣,選擇未來。他走了,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,仍在這裡。
內文搜尋
X